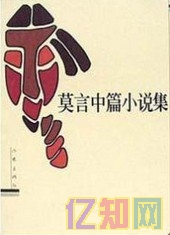
《野骡子》中,莫言并没有特别强调的故事发生的背景,但是很显然改革开放初期的迷惑与困扰已经跃然纸上。改革开放初期的民间社会,并没有摆脱生产队大锅饭的影响,也并没有树立全民奔向小康社会的决心。当“土改”、“致富”、“饥饿”、“注水肉”这些意象还在农民的脑子中碰撞的时候,价值观念与道德标准也经历了颠覆与重生的过程。
《野骡子》首先表现出来的,就是生存观念的碰撞。在计划经济土崩瓦解,市场经济尚未完善的大环境下,那些生活在民间的老百姓无疑是最彷徨最困惑的群体。莫言通过《野骡子》展现的,也是普通农民的困惑和前途未卜的恐慌。
《野骡子》中关于生存观念问题最突出的表现在我的父亲罗通与我的母亲杨玉珍的身上。 “勤俭持家”与“及时行乐”,母亲与父亲的生存观念的碰撞也绝不是个别的现象,他们代表着整个农村社会在社会的转型期对于前途的困惑。每个人的心中都会有自己的小算盘,并不是谁说“大踏步奔向共产主义”就会一往无前的跟着走。他们看重的是自己的利益,是切身的利害关系。这种态度被很多人称为是小农意思,是农民思想落后的表现。但是,这就是民间的意识,就是切实存在于广大民众中间的切实存在。
《野骡子》抓住了这一点,这种民间的意识不是口号也不是标语,更不是简单概念,莫言将这种活生生的存在搬到了小说的文字中。所以他的作品是真实的,是令人信服的。
莫言在叙述整个屠宰村都往肉中注水的事件时,我们看不到他的观点,他没有对这件事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或对或错。当然,《野骡子》也并不是零度情感的介入,它所表现出来的是民间道德观念的特有标准,即对传统道德观念的颠覆与消解。
在这个靠卖注水肉发家致富的村子,传统的道德观念就不会很强烈,就注定不会有像《白鹿原》所描绘的那些族长、祠堂、道德卫士。村长老兰因为发明了利用高压水泵往动物尸体里强行注水的科学方法,而在村子里颇有威望。“村里人有骂他的,有贴小字报攻击他的,也有写人民来信控告他的,但拥护他的人远比反对他的人多。”
再有就是村里人对于牛贩子来路的讳莫如深。牛贩子的来路其实早已不是秘密,每次都运来大牛、小牛,甚至还有正在喂奶的母牛,他们的身份也相当明晰。“少年时代的我曾经就这个问题问过我的父母和村子里那些白了胡子的老人,他们总是瞪着眼看着我,好像我问他们的问题深奥得无法回答或者简单得不需要回答。”牛贩子并不是贩牛,而是偷牛,这已经不是秘密了,但为什么没有人戳穿这一现象呢?这就是民间的独特的景象。萧红曾经在《呼兰河传》中有过类似的描述。因为有大泥泡子的存在,所以人们吃瘟猪肉才会有理由,因为那肯定是“大水泡子又淹死猪了”。
虽然在《野骡子》中,莫言所描绘的父亲是一个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的、潇洒的流氓角色,但是这并不妨碍“父亲”这一形象的高大与理想化。因为小说是通过罗小通这一儿童的视角来展现父亲这一角色的。
在小说的开头,与野骡子姑姑私奔的父亲的形象在叙述者罗小通的意念里仍然是美好的。“五年中流传到我耳朵里的关于父亲与野骡子的谣言何止二百条,但我念念不忘并且反复品味的,也就是前边所说的那三条……”。 “在炉子上煮狍子肉,父亲的脸和野骡子的脸被炉火映得红彤彤的,好像抹上了一层红颜色”,“他们在蒙古包里,点起一堆牛屎火,火上吊着铁锅,锅里炖着肥牛肉,肉香扑鼻,他们一边吃肉一边喝着浓浓的奶茶”,“煮上一锅肥狗肉,启开一瓶白酒,每人握着一条狗腿,端着一碗白酒,他们喝一口白酒啃一口肥狗肉,撑得腮帮子鼓鼓的,好像油光光的小皮球……”无论哪一条留言,都依托着叙述者罗小通对于父亲的怀念以及对父亲的境遇的理想化。跟着父亲就会有肉吃而且活得潇洒,这是罗小通的信念。
那是什么给他这样坚定的信念呢?父亲的聪明。小通认为“父亲是人中之龙,而人中之龙是不不屑积攒家产的。”“人们见过松鼠、耗子之类的小野兽挖地洞储存粮食,谁见过兽中之王老虎挖地洞储存粮食?”父亲善于牯牛,并且消除了牲畜交易市场的模糊性,一举将那些古老的经纪人赶下了历史的舞台。父亲与村长老兰的斗法,不但在情场上得胜。而且在打谷场上面对老兰几乎侮辱的挑衅,竟能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获胜,父亲的声誉也在小通的心中达到顶峰。
村长老兰在小说中的重要角色,在短短的3万字的小说中,老兰就有清早教母亲学开拖拉机和在打谷场与父亲斗法两段细节的描写,戏份儿不可谓不多。而且,老兰作为背景人物在小说中出现了无数次。作为全村黑心致富的带头人,老兰无私的将高压注水的方法传授给众乡亲,却留了一手。致使他既能借此当上村长,“拥护他的人远比反对他的人多”,又能保持威望,因为“同样是注水肉,但他的肉色泽鲜美,气味芬芳,放在烈日下暴晒两天也不会腐败变质,而别人的肉一天卖不出去就会发臭生蛆。”
如果说小说中还在追寻“父性”的回归的话,那么老兰无疑是那个合适的人选。他对技艺的无私传递;他摒弃前嫌,将拖拉机以废铁的价格买个罗通家的;他将全村的老少爷们儿统领起来,共同致富。但是在小说中,并不能读出对于老兰的赞颂。可以说这是莫言的独到之处,也是他的困惑。也许这样一个黑心致富的带头人并不是他要着力推崇的,但是,民间的独特的价值观念又将他推到了荣誉与地位的顶峰。
不论是父亲还是老兰,都并不是一个可以被看成是代表某种父性回归的个体,但是莫言在他们身上倾注的感情并作了“父性”回归的尝试确实不争的事实。莫言甚至男性至于农村,至于民间的意义,父性的追求与回归是他不能回避的课题。
从传统价值观念的颠覆到父性的回归,莫言在《野骡子》中始终坚持的,就是其民间立场。以老百姓的视角看待社会人生,以老百姓的观念展现农村生活,这是《野骡子》带给我们的最直观的感受。
作者简介:
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2月17日生,山东高密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他自上世纪80年代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
他的《红高粱》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坛的里程碑之作,已经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2011年莫言荣获茅盾文学奖。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是:“通过幻觉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

